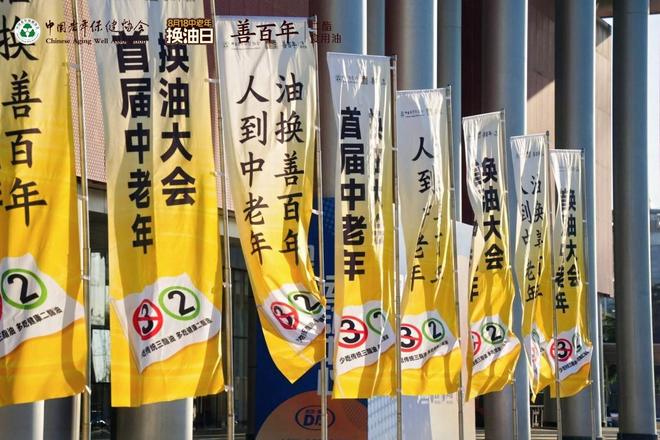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这句名言,经常成为论证人的政治性存在的论据。但与现代政治学不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建立在另一个核心概念之上:城邦。城邦的古希腊语是πόλις,这个词也是政治学(politics)词根的由来。换言之,政治学就是城邦之学。当亚里士多德说人依其自然(或者说依其本性),是政治的动物时,其实就代表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一个自然特征,就是人类生活在城邦里,人是在城邦生活的动物。不过,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抵达政治的要义。因为在城邦里生活的不只有人,也有其他动物以及奴隶(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奴隶是算不上人的)。仅仅从生理学和地理范围来确定人的政治本性,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界定另一个范围。亚里士多德其实还写过一本书叫《家政学》。有趣的是,这里的家政学就是economics,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的意思变成了经济学。但家政学的古希腊语的词根οίκος,意思是“家”或“房子”。而总体上,家政学是处理家族内部事务的学问。换言之,家政学与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密切相关,家庭是自然血统的延续,在这个基础上,家政学面对的是带有生物学意义上亲缘性的群体。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家与城邦、家政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家庭和城邦都是群体。但家庭或家族的核心是血缘关系,它带有天然的亲缘性,因此家族的血脉与忠诚成为最狠心的价值;但城邦不同,城邦是陌生人的团体,他们之间没有天然的亲缘性,让这些没有血缘亲缘性的个体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并不是自然的成就,而是人类自己的成就。换言之,动物也有群体,例如蚂蚁、黄蜂、猴子、狼等,但这些动物的群体仍然依附于血缘性的家族关系;而人类的城邦不同,人类的城邦一开始就需要摆脱这种自然血缘的设定,指向一个更高的目标,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说:“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6]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人类的共同存在,并不是依赖于自然血缘的家族关系,而是在家族解体之后的个体彼此间形成的政治关系。城邦建立在这种政治关系之上,让不同的人说着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法度,沿袭共同的习俗,信奉共同的信念。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群学,即政治学。
尽管今天的政治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拨开诸多复杂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理论最内核处,仍然是一种群学。人们并不是遭遇一个他者,就能天生地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换言之,我们能与其他人(陌生人)生活在一个空间里,是需要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人类共同体成为城邦的缘由。其实,早在吴冠军教授的早期著作中,他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在《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一书中,吴冠军教授就已经提出了:“可见,人和人并不直接地就‘自然’在一起——根据霍布斯,那种‘自然状态’会是人与人像狼和狼一样地无止境地互相争斗、厮杀。‘人道’之于‘禽兽之行’的差别就在于:人和人总是通过一个神秘的、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X而彼此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定的秩序、一个‘世界’;而不是像禽兽那般互相撕斗,最后死在一起,或者像石块那样,彻底‘无世界性’地存在。群学,就是研究这个X的学问。”[7]所以,对群学的关注,一直都是吴冠军教授关心的主题。之前,吴冠军教授更多是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齐泽克的哲学入手,来探讨人类何以为群的问题。不过,在最新出版的《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一书中,他进一步将群学的问题加以升华。譬如,他指出《荀子·王制》中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8]127,提出了“智人的‘有智’,就在于‘能群’”[1]59。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动物和人类的区别在于智人,智人能够超越动物的贫乏世界,从而筑造一个人工的家园,这个家园实际上就是能群的城邦。但人类依赖于什么才能筑造一个世界,即“人何以能群?”我们可以将荀子的话引述完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8]127。荀子的意思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体,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分别的,这是一条区分的标准,将人与非人区别开来,这就是所谓的分。但在荀子这些带有古代儒家士人气息的学者那里,区分的标准只有一个:义。这个回答显然回到了儒家经典的意识形态。但吴冠军教授在这里关注的重点,既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城邦的正义,也不是荀子所谓的义,而是一个X。总存在着一个X,让人与非人区分开来。这些具有X特征的人,成为共同体或群之内的人;相反,那些不具有X特征的人,即便具有人类的躯体,也不能成为群的一部分。因此,群学在根本上不同于生物学上定义的人类学,它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性的。用阿甘本的话来说,这个X就是一个生命政治的装置,“通过它,让生命归属于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就是存在降临在政治维度上……它关联了存在,并让其进行运动,与之对应的是生命政治装置,它关联了生命,并让生命政治化”[9]。简言之,让城邦成为城邦、让群成为群的,就是一套装置、一个区分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就获得了政治的外衣,即bios,否则就只是一个赤裸生命,即zoē。因此,政治学核心并不在于如何将城邦和共同体建立成符合良善观念的群,这只是政治学的表象。真正的政治学必然是血淋淋和残忍的。它是不顾一切将不同人分成符合X的bios,以及不符合X的赤裸生命zoē的构成。拥有X的个体构成了可以交流、贸易、诉讼、娱乐、教育、传承的群,只有他们才能拥有谈论政治的理念,追求良善正义的美好蓝图;而那些赤裸生命只能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成为蛰伏在臭水沟中的蛆虫。
亚里士多德、荀子谈到的能群的X,多半是抽象的观念,如正义、善、义等。在中世纪,宗教也成为一个X,但在今天,这个X显然已经成为技术的专长。这种现象并不是在数字时代才出现的,当西方的殖民者在船坚炮利的现代工业产品的加持下,征服了广大的亚非拉地域时,他们实际上将能够使用现代技术的人与不能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加以区分,前者是文明人(the civilized),而后者是野蛮人(the savage)。只有拥有和理解这些技术的人,才能是文明社会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当然也有相对应的政治理念,如政治自由、权利、分配正义等,但最根本的X恰恰是,这些文明人都无一例外地纳入现代政治治理的装置之下。这就是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个X的装置之下,生产了现代主体性,而现代主体性就是一种技术主体性,一个被现代技术装置支配着的主体。因此,阿甘本说:“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相同的个体,以及相同的实体,可以是多重主体化进程的场所:手机的使用者、网络冲浪者、小说家、探戈迷、反全球化的活动分子等等。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装置的无限增长,与主体化进程同等程度的扩散是一致的。”[10]这样,今天的政治学俨然是一个在技术装置下不断生产出符合能群标准的主体的政治学,这就是政治越来越成为技术—政治的原因。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模仿荀子的口吻问道:“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技术。”在此,我们可以完全接受吴冠军教授的判断:“这就是晚近技术—政治状况所发生的关键变化:技术成为政治的根本性状况(而非仅仅是影响后者的要素之一)。在智慧城市中,技术器官直接变成政治器官。”[1]71这就是能群的技术—政治。原先作为政治之分的诸多观念,无论是正义,还是宗教,是自由,还是权利,如今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技术尤其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所取代。人类的未来共同体的诸多方案,是在技术层面上来治理的,人类分配的矛盾也是在技术层面上解决的。换言之,人类共同体越来越多根本问题,都必须建立在技术的奠基之上。人何以能群的问题变成技术的答案。能群的技术—政治正在日益兴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时,分解出了心理、科学技术以及政治学三个维度。然而,这三个维度越来越被技术一个维度所统御,成为技术—政治的分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距离和触感,已经被手机屏幕和键盘鼠标的触感所取代;人与人直面的视觉,也逐渐被监控视频的人脸扫描和屏幕上的美颜画面所支配。人与人之间已经被技术所中介和支配,技术成为我们能群的重要尺度。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希冀的未来社会,我们仍然需要在技术—政治上留存一点属于人性的温度。
技术—政治的直接后果是全社会的所有个体都需要通过技术的中介来实现各种联结和沟通,生产和消费行为也必须依赖于技术平台来实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卢卡奇笔下人被商品化的物化现象,也不是德波的景观化的堆积,而是一种全新的技术透明社会。原先依赖于信仰、观念和善建立起来的人类共同体,如今完全被技术所取代,变成了全景敞视的透明社会。这就是德国韩裔学者韩炳哲所提出的“透明社会”:“如今的监控社会有一个独特的全景结构。与相互孤立的边沁式全景监狱里的犯人不同,监控社会的居民互相联网,彼此交流。为透明提供保障的不是孤单和独立,而是超交际。最重要的是,数字化全景监狱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居民们通过自我展示和自己揭露,参与到它的建造和运营之中。他们在全景市场上展示自己。”[11]在韩炳哲的描述中,技术—政治为人类带来的不是解放,不是幸福的福祉,而是巨大的控制装置;人们只有经过平台的算法,才能显示自己,才能与其他人交流。他们所接触到的朋友圈,都是经过算法精密分配和匹配好的。在相亲网站上,智能算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门当户对,一个相亲的用户,不可能看到比自己条件好很多或差很多的其他用户。在滴滴打车软件中,乘客的等级和司机的等级也具有对应性,即便在玩《王者荣耀》这样的匹配玩家的游戏时,也只有同等级别的玩家才有资格被分配到同一个战斗副本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明白,这不是我们所希冀的社会,我们不是一个巨大机器下的蚂蚁,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人类。
当然,对技术—政治的这种认识,不能在原先的启蒙理性框架下来完成。因为自从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等人的解构和重构之后,启蒙理性已经随着宏大叙事的框架崩溃而土崩瓦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批判框架,一种让人类重新掌握自己的温度和节奏的批判框架。这是一种后人类的批判框架。正如吴冠军教授指出:“这就是后人类主义在思想史上关键价值之所在:‘后人类’(并不仅仅只是“赛博格”),激进地刺出了人类主义框架。真正的批判,永远是对框架本身的挑战,而不是对内容的增减。启蒙主义者和当代新启蒙主义者尽管在把各种个体与群体纳入‘人’的框架上取得了成绩,然而只要‘中心—边缘’架构不被破除,就永远会有结构性的余数。”[1]26吴冠军教授的新批判理论,是对笛卡儿、康德以降的启蒙理性的质疑,因为这种启蒙理性将批判性的框架建立在自主的理性人的基础上,而这种理性人所对应的社会秩序就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机器已经变成了陈旧的废铁,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已经变成了工业遗迹;而那些信奉着这些信条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那种曾经熠熠生辉的经济人的理性已经无法召唤出共同体的魔法,让人们组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市民社会。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只能面对着手机和电脑屏幕的“御宅族”(东浩纪语)。他们的幸福不在于现实世界的生产和消费,而是在网络和虚拟世界中的交际和拼杀。现实被冷漠化了,《黑客帝国》中著名的台词“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无意中一语成谶,成为这个智能化和数字化社会的谶言。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技术—政治,但如何超越呢?吴冠军教授在《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爱。这不是吴冠军教授第一次关注爱的问题,早在他的《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中,他对于爱的定义是:“爱,便正是这样一个例外状态、一个溢出性的‘非常’状态、一个永远的紧急状态。爱,打断了原先的‘正常生活’之连贯运转:它剧烈地扰乱了既定的工作程序(‘日常’事务)、刺破了既有的生活部署(‘现实’常规)。在爱中的人,不再有原先每日生活中的那种‘合理’的程序化的‘平衡’,而是瞬间处身于狂潮般涌来的暴风骤雨之中、处于那‘日常’状态的一个深渊性的缺口之中——这个缺口,即标示了原先那周而复始的每日生活的一个根本性缺失。”[12]吴冠军教授的爱,并不是人与人之间滥俗化的爱情,而是一种超越常规秩序的例外,一种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的情感。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同于世界中的万物,就是人可以被情感之爱所触动,而这种被触动的力量,自然也成为超越正常秩序的潜能。在《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中,吴冠军教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命题。因为在智能算法面前,那种对主体规训化和常规化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不断得到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这种作为例外状态溢出的爱。吴冠军教授指出:“‘算法’(algorithm)一词,被用来指一套有输入、有输出的解决问题的计算步骤。然而,爱的问题,显然很难被算法化处理——无法描述清楚爱是什么,便无从清晰界定要输入哪些变量信息。”[1]241爱的确是一种溢出,也具有将人们重新连接起来,产生身体性情动(affect)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爱的情感,的确是智能技术时代下技术—政治所无法完全捕捉到的东西。尽管有人试图用算法来计算人的感情因素,但爱的情感会在算法面前暴露出一种无法预料的激进性,这就是斯雷奇科·霍瓦特(Srecko Horvat)的爱的激进性。霍瓦特说:“这就是爱的第一个根本性后果: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你整个日常生活的基础,过去和未来,都会被这个新的当下所抹除,它重新构成了你的过去和未来。但这还是爱吗?不,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这是可能转化为‘爱’的事物的第一个根本性后果。”[13]换言之,无论在吴冠军教授那里,还是在霍瓦特那里,爱的潜能在于,它创造了另一个当下、另一种自我,或者说另一种共同体。吴冠军教授指出:“黑箱性的爱,是激进的、彻底无理性的怪物——哪怕是个‘最谨小慎微的疯狂’,也会让爱者冲出理性轨道而亲吻死亡。”[1]289总而言之,它创造了另一种人类;准确地说,爱已经超越了人类理性的限度,这是后人类的激进性。
正是在这里,我们与吴冠军教授分道扬镳了。通过爱走向后人类,走向激进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政治,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无论是世间的滥俗之爱,还是被吴冠军教授以及阿兰·巴迪欧、易洛思、霍瓦特等人赋予了激进性的爱,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无法落实的抽象之爱,不是普通人的情感。它们被赋予了过多的浪漫化色彩。犹如在工业文明滥觞时期的浪漫主义一样,这种在小说和绘画中展现的田园诗歌的爱情故事,并不能帮助人们抵御资本主义对底层无产者的剥削和掠夺。中产阶级的浪漫幻想不可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一样:“可是爱啊!——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14]魏特林、费尔巴哈都十分相信通过爱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这也成为巴迪欧、易洛思、霍瓦特等人的希冀,但爱的激进性不能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实在性,也不可能存在着超越一切区分的爱。
与此同时,当吴冠军教授认为爱是可以摆脱算法理性控制的潜能的时候,实际上忽略了人类历史上的暴力、残忍、怯懦等也超越了算法理性,但我们不能将这些东西作为改变人类社会的潜能。那些超越算法理性的溢出,是否也有优劣之分呢?是什么让这些社会批判理论家钦慕爱,而否定暴力、残忍和怯懦,显得如此厚此薄彼呢?其实走向后人类的根本,不在于爱,尽管爱对于创立一个有序的后人类社会是必然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人类何以能够与超越人类的智能体交流和共存,就像我们可以通过在游戏中的对战,了解动物的动作反应的图式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盲目溢出的爱,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爱的泛滥,而是如何让人类进化到可以与智能体交流和共存的地步,让人类也可以掌握在深度学习的黑箱中形成的智能算法的结构,并将之综合到人类的神经网络算法中。这就是斯蒂格勒、许煜等人提出的宇宙技术问题,我们的问题源自技术,让我们陷于技术—政治藩篱的,也是技术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人类不真正面对技术及其环境的存在,我们就无法真正走向后人类,技术物和技术主体都是后种系生成的进化,我们的未来是在外在化器官的辅助下,让我们身体与技术合成赛博格,成为巨大行星运算体系的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未来。
[1]吴冠军.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2][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André Leroi-Gourhan,Gesture and Speech,trans.A.B.Berger,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1993,p.139.
[4][意]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33.
[5]关于海德格尔对于动物的“贫乏世界”的描述,参见[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M].赵卫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36.另外,原书将“贫乏世界”翻译为“缺乏世界”,而将“筑造世界”翻译为“形成着世界”,在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为了全文的统一性,沿用了“贫乏世界”和“筑造世界”的译法。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
[7]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6.
[8]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Giorgio Agamben,The Use of Bodies,trans.Adam Kotsko,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04.
[10][意]吉奥乔·阿甘本.论友爱[M].刘耀辉,尉光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8.
[11][德]韩炳哲.透明社会[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79.
[12]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3.
[13]Srecko Horvat,The Radicality of Love,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6,pp.147-148.
[14][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