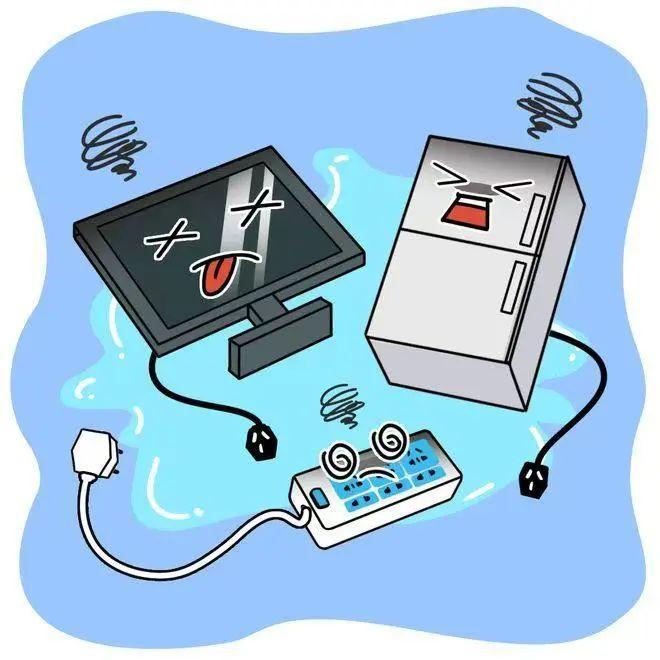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行踪诡秘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先去他最常出现、最活跃的地方,摸清他的相貌、习惯和行为模式,为他建立一份精准的“用户画像”。
研究人员正是采用了这种策略。他们知道,在生命早期,海马体的神经新生现象是毋庸置疑的,活跃且数量众多。因此,他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了0到5岁的婴幼儿和儿童。这个阶段的大脑,就像一张内容最丰富、标记最清晰的“新生藏宝图”。
他们收集了6名婴幼儿的离世后捐献的海马体组织,利用单细胞核RNA测序 (single-nucleus RNA sequencing, snRNA-seq),一次性分析了高达115,861个细胞核的基因表达情况。这项技术可以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瞬间,每个细胞核里有哪些基因正在“开工”(即被转录成RNA)。这就像是为大脑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拍下了一张详细的工作快照。
当所有细胞的数据汇集在一起时,一幅壮观的“细胞星图”便展现在眼前。在这张图上,功能相似的细胞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不同的“星座”,例如兴奋性神经元、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等等。
研究人员的目光迅速锁定在了那些表达神经新生相关基因的细胞“星座”上。他们发现,巨大的星形胶质细胞群和颗粒神经元群之间,仿佛有一条由“星尘”连接成的微弱轨迹。当他们放大这条轨迹时,惊喜出现了:这里散落着一些正在表达增殖标记基因 MKI67 和前体细胞特征基因 EOMES 的细胞。MKI67 是细胞正在分裂的“铁证”,而 EOMES 则是神经前体细胞的一个重要身份标识。
这还不够。为了确认这些细胞的“人生轨迹”,研究人员动用了一项名为RNA速度 (RNA velocity) 的分析技术。这项技术能通过分析细胞内未成熟和已成熟的RNA比例,预测出细胞在未来短时间内的分化方向。结果令人振奋:分析显示,这些细胞的“命运之箭”清晰地从表达干细胞标记的状态,指向了神经前体细胞,再奔向新生的颗粒神经元。这完美地勾勒出了一条从“种子”到“果实”的完整分化路径。
通过这次在儿童大脑中的“演习”,研究人员成功地为不同阶段的新生细胞绘制了详尽的“分子身份证”:神经干细胞 (Neural Stem Cells, NSC),它们是源头,表达着 NESTIN, PAX6, SOX2 等“干性”基因;中间前体细胞 (Intermediate Progenitors, INP),它们是活跃的“增殖工厂”,高表达 MKI67 和 EOMES;神经母细胞 (Neuroblasts, NB),它们是“学徒期”的神经元,开始表达 DCX 等神经元早期标记;以及未成熟颗粒神经元 (Immature Granule Neurons, ImmGN),它们是“新兵”,逐渐显现出成熟神经元的功能特征。
这份来自童年大脑的“新生图谱”,为接下来在成人大脑这片更具挑战性的“无人区”中的探索,提供了最宝贵的导航和识别工具。
有了儿童时期的清晰图谱,识别成人大脑中的新生细胞,不就易如反掌了吗?事实远非如此。成人大脑中的神经前体细胞极其稀少,据估计可能只占海马体总细胞数的极小一部分。在数以百万计的细胞中寻找这寥寥无几的“新生火种”,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此前的许多研究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测序的细胞数量不够多,这些稀有细胞在数据分析的“噪音”中被淹没了。
面对这一巨大挑战,研究团队祭出了两大“杀手锏”。
第一招:富集!先用“磁力鱼钩”把针吸出来。
既然针太少,那就想办法先把针富集起来再捞。研究人员利用了荧光激活细胞分选 (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技术。他们巧妙地使用了一种能特异性结合 Ki67 蛋白(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增殖标记)的抗体,并给这个抗体带上荧光。当把成人海马体的所有细胞核悬液流过分选仪器时,那些正在分裂增殖、表达Ki67的细胞核就会被荧光标记,并被仪器精准地“捕捞”出来。
效果是惊人的。通过这种方法,样本中表达 MKI67 基因的细胞核比例被富集了整整37倍!这极大地增加了在后续测序中“撞见”这些稀有增殖细胞的概率。
第二招:AI识别!训练一个“前体细胞侦探”。
即便经过富集,这些细胞依然是少数派,且混杂在其他类型的增殖细胞(如内皮细胞、胶质细胞)中,难以辨认。这时,研究团队亮出了他们的第二个王牌: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他们将在儿童数据集中识别出的神经前体细胞(INPs和神经母细胞)作为“标准答案”,训练了一个人工智能算法。这个算法学习了这些前体细胞独特的基因表达模式——也就是它们的“分子指纹”。它变成了一个高度灵敏的“前体细胞侦探”,能够在一大堆复杂的细胞数据中,准确地找出那些与儿童期前体细胞“长得最像”的细胞。
为了确保这位AI侦探不是个“冒失鬼”,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培训”和“压力测试”。他们先让它去分析一个已知的、存在神经新生的小鼠海马体数据集,结果AI成功识别了其中91%的增殖性前体细胞,且误判率极低。接着,他们又让AI去分析不存在神经新生的人类成年大脑皮层数据,在超过10万个细胞中,AI几乎没有做出任何错误的“指控”。
这一系列测试证明,这个AI侦探不仅火眼金睛,而且行事谨慎,完全有能力在包含19名成人(年龄横跨13至78岁)、总计超过40万个细胞核的庞大数据集中,揪出那些隐藏极深的神经前体细胞。
在这位AI侦探的帮助下,研究人员最终在所有成人和青少年的样本中,共鉴定出了354个珍贵的神经前体细胞。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这已是历史性的突破。
那么,这些在成年人大脑中找到的“新生火种”,和儿童时期的、以及其他物种的相比,是“同款”吗?还是某种特有的“限量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跨物种大整合”。他们将本次研究获得的人类数据,与已发表的小鼠、猪和恒河猴的海马体单细胞数据整合到一起进行分析。这就像是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神经新生细胞家族派对”,让来自不同物种、不同年龄的细胞成员齐聚一堂。
结果显示,无论是人类儿童、成人,还是小鼠、猪和猴子,它们的神经干细胞、INPs和神经母细胞在基因表达上都高度相似,在数据可视化的“细胞星图”上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跨物种的“新生细胞大家族”。这说明,海马体的神经新生是一个在哺乳动物中相当古老且保守的生物学过程。
当然,细节处也存在有趣的物种差异。例如,一个名为HES6的基因,在小鼠中主要在INP和神经母细胞阶段表达,而在人类的儿童海马体中,它在更早的神经干细胞阶段就已经“上岗”了。此外,与儿童相比,成年人的增殖性前体细胞表达的 EOMES 和 TFAP2C(两个关键的前体细胞基因)水平较低,但它们也表达一些儿童前体细胞中不常见的“新”基因,例如APOLD1和RRM2。
这些细微的差别,可能正反映了不同物种、不同生命阶段神经新生调控的精妙之处,也为我们理解人类神经发生的独特性提供了新的线索。
更重要的是,当把所有这些细胞放在一个模拟分化过程的“时间轴”上时,研究人员发现,从神经干细胞到INP,再到神经母细胞,最终走向年轻神经元,这条分化路径在所有物种和年龄段中都惊人地一致。成年人大脑中新发现的前体细胞,也完美地镶嵌在这条经典的路径上,它们不是迷失的“孤儿”,而是这条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都来自于打碎组织后获得的细胞核悬液测序。这就像我们虽然知道了一个城市里有哪些人,但并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街区,从事什么工作。为了让证据链更加完整,研究人员需要回答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在数据中被识别出的前体细胞,在真实的大脑组织中,究竟位于何处?它们是否真的在神经新生应该发生的“摇篮”——齿状回 (dentate gyrus) 的颗粒细胞层附近?
为了实现细胞的“原位”识别,研究人员动用了空间转录组学 (spatial transcriptomics) 技术:RNAscope 和 Xenium。这些技术就像是为大脑组织配备了“细胞级GPS”,能够让我们在组织切片上,直接看到每个细胞内特定RNA分子的位置和数量。
这让研究人员得以在保持组织完整结构的情况下,直接在成人海马体切片上寻找那些带有特定“分子身份证”的细胞。例如,一个同时表达 NESTIN、SOX2 和 ASCL1 三种基因的细胞,极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神经干细胞。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真的“抓了个现行”!他们找到了神经干细胞(NSC),这些细胞零星地分布在齿状回的特定区域;他们找到了中间前体细胞(INP),其中一些细胞同时还表达着增殖标记 MKI67!这意味着它们正在积极地分裂,并且常常成对或以小簇的形式出现;他们也找到了神经母细胞(NB),其中一些也携带着 MKI67 的增殖信号。
此外,他们还发现了许多之前未被充分认识的新标记物,例如EZH2,它在增殖的早期INP和神经母细胞中都有表达;还有GLRA2 和 EPHA3,它们在晚期的神经母细胞和未成熟神经元中出现。这些新发现的标记,为未来研究人类神经新生提供了更精准的“探测器”。
最终,通过这些空间定位技术,研究团队在所有被检测的10名成人样本中,都找到了神经前体细胞存在的证据。它们就潜伏在海马体齿状回的颗粒细胞层及其邻近的门区,这正是理论上神经新生发生的“热点区域”。数据分析中的虚拟细胞,终于在真实的大脑组织中找到了它们的“家”。
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和严谨性,为“成人海马体神经新生”这一长达数十年的科学辩论画上了一个坚实的逗号,而非句号。它通过整合大样本测序、巧妙的细胞富集、精准的机器学习算法和强大的空间定位技术,构建了一个完整且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证明了:在人类直到老年时期的大脑中,依然存在着一个具备增殖和分化潜能的神经前体细胞库,它们是海马体持续“上新”神经元的细胞来源。
这项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平息一场学术争论。它为我们理解大脑的功能和疾病打开了全新的大门。我们知道,海马体是记忆的港湾,是情绪的调节阀。那些新生的神经元,被认为在学习新知识、形成新记忆、以及从压力和抑郁中恢复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项研究首次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新生细胞的“零件清单”和“成长路线图”,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索它们的功能。
研究中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成人神经新生的水平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 例如,一位有癫痫病史的40岁捐献者,其大脑中的前体细胞数量就明显高于其他同龄人,这与“癫痫可能刺激神经新生”的既有假说相符。而在另一些看似健康的个体中,前体细胞的数量则非常少。这些差异背后,是遗传、生活方式、还是疾病状态在起作用?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迷人问题。
未来,基于这项研究发现的细胞标记物和分化路径,研究人员或许可以开发出新的方法,来监测甚至调控人类大脑的神经新生过程。这对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等与海马体功能受损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无疑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的大脑,并非一台一成不变的机器。在它的深处,生命的创造力从未停歇。即便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在我们经历喜怒哀乐的每一天,总有那么一些微小而坚韧的“种子”,在悄然萌发,为我们的大脑注入新的活力和可能。这本身,就是生命最动人的诗篇。
参考文献